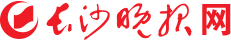病友
吴凯风
他跟我住同一个病房,是建筑工人。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疾病稍微压弯了脊梁,他是个典型的五大三粗的壮汉,身材笔挺、魁梧,只是鼻梁上佩戴的那副金属架眼镜,暴露了他的内敛性格和文人气质。
他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失业,机器设备抢走了人工给墙面抹灰的活。前几年,他一直在长沙,活多,干不完。他今年破例去郴州给墙面抹灰,这是他从业以来的第一次。在他看来,去郴州揽活,不啻一次远征。
前一个在他那张病床躺了三天的病友刚康复出院,他就掐着时间点,只身走进了病房,比我晚到两三个小时。护士为他换上了新的洁白的床单和被褥。他躺了上去,捧着手机刷短视频,等候医生前来问诊。
他的病情初看比我严重,下一级医院没把握接诊,把他转到这家市级医院。医生进来问诊时的队伍也庞大,一个年轻的管床医生带了三四个实习生。
他描述的病情,与我前段在网上查询了解到的某种恶性肿瘤症状十分吻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发现身边有一普遍现象: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条件不断变好,人们对疾病似乎越来越恐惧。
前段身体不适,上网一查,网络就给我推送了很多关于这种恶性肿瘤的知识。尽管我表现出来的症状,与网上的描述有差别,但还是让我的神经在一段时间内绷得紧紧的。更夸张的是,我一个年轻的同事,有一天出现腹泻,就紧张兮兮,愁眉苦脸地跟我们说,是不是患了癌症,马上请假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医生问诊后,给他开了CT检查,叮嘱他从现在起不要吃东西,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诊。他如临大敌,精神萎靡,卧倒在床上,闭上眼睛,不再刷手机短视频。
我安慰他,我此前也在他就诊的那个下一级医院做过检查。
他仿佛遇到了知音,精神稍有振作。告诉我,他在工地上干活,天气太热,喝了一瓶冰啤酒,就肚子疼、呕吐、腹泻,吃了几天药,没见好转。
他妻子把当天工地上的活干完,赶来了医院,个子不高,微胖身材,给他带来了住院所需的生活物品,一口新化方言。与我属同一方言区,这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夫妻俩即使用方言交流,也不妨碍“隔床有耳”,我都听得懂。
晚上,给他打电话问候的工友很多。接通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粗声粗气似问非问的“什么情况”,第二句话就是“要不要给你带两瓶啤酒,搞点烧烤过来”。他想笑,却笑不出来,低声回应。医生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他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妻子心里也压着同一块石头,坐在床沿,背对着他,不时发出一两声叹气,可能眼里早就噙满了泪水。
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做完了手术,静养两天就可以出院。他是下午做完了检查,不需要手术,取了样送去做活检,晚上可以吃些流质食物。我说,活检是这类检查都需要的,不用担心。夫妻俩松了一口气,妻子说,他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晚餐,妻子去街上买了一碗小米粥和一包方便面。他们问我,岳麓山是不是就在附近?我说是的。岳麓山要不要收门票?我说不要。他们给儿子打电话,说明天跟舅舅一起过来,去爬岳麓山。
儿子暑假寄养在长沙的舅舅家里。他们在长沙城里生活打拼多年,住的是简易工棚。他们说,现在条件好了,工棚里装了空调,他们没有爬过一次岳麓山。
晚上十点左右,他的输液瓶滴完了这一天的最后一滴药液。妻子躺在床上,已经睡着,工地上繁重的活计,困乏了她的身体。他起身走出病房,尽管手上扎着留置针,但没有了输液管的牵绊,也算是获得了片刻的自由。他在病房外转了一圈,回来时若有所得。
妻子醒了,睡眼惺忪,抱歉地说睡着了,似在喃喃呓语。又问:“药打完了?”他看着妻子,问她,你饿不饿?妻子说不饿。旋即大悟,反问,你饿了?他说,有点饿。
“你饿不饿”,这一提问很有艺术性,出发点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妻子大悟后反问,也有灵犀。平凡如他们夫妻俩,生活中的相知与相爱,足可以抵消病房内外的不少苦难。
他们走出医院,挤进了外面还依然热闹的街市。这是他们来长沙后,第一次在深夜相拥相依品味城市的五光十色。我有点怀疑,他抓住片刻的自由,去病房外走一圈,透过医院的窗户,看到了外面的灯红酒绿,他的“有点饿”,只是想趁机带妻子去街上走一走的借口。
他们回来时,我从睡梦中惊醒,时间已是半夜一点。在病床上,人们总是睡不踏实。他们第二天没有去爬岳麓山,儿子说,舅舅要去单位加班,抽不出时间带他过来。
他们在电话里承诺,下次一定带儿子去爬岳麓山,去看岳麓书院。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