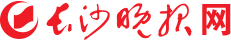散文 | 晴雨张家界
■彭汝南
车行半路,突遇暴雨。
刚才还是刺眼火辣的阳光,忽地就钻入电闪雷鸣之中。暴雨如瀑,狠狠地砸向车窗,雨刷急速挥动,仍看不清前方的路。
车内孩子们忘了顽皮,忘了颤抖,忘了兴奋,傻傻地看着窗外。暴雨冲刷着田野,黑云笼罩着山脉,雨幕如墙、如帆、如在厮杀的一片苍穹,这是一片城市孩子从未见过的辽阔旷野。
还未等孩子们回过味来,车就钻出暴雨下的黑暗森林,路面干燥,天高地阔,远处山丘起伏,有几缕阳光透过高高薄薄的乌云,散落在田野之上,仿佛天未曾黑过、雨未曾落下。
孩子们觉得刚才只不过是愣了一个神、做了一个梦,又开始喧闹起来。
不知何时,暴雨又砸向车顶,电闪雷鸣。
如此反复。
雨又下起来了,好在可以看一台节目。现在的雨不大、不小,就像平铺直叙的八股文,毫无感情、均匀洒在舞台上。音乐优美,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舞台上到处走,时不时还抬抬手、踢踢腿,有时还跳两下。舞台巨大,在两山之间,一侧的山居灯火通明,错落有致,在旋律下显得美丽而又神秘。而另一侧却群山环绕,一眼望不到边。
雨就这么毫无感情地下着,舞台上的演员时多时少,在雨幕下到处乱走——我很担心他们会不小心滑倒。伴随着美丽的音乐,冗长的表演终于结束了,巨大的光柱突然亮了起来,看到了深夜的天门山。
孩子们长长出了一口气,闹着去休息,我们一直还没有到住的地方。
在不大不小均匀的雨中,在深深的夜幕里,车静谧地行驶,孩子们终于安静下来。一幕幕景色快速飞过——市区灯光下的雨幕、黑暗山坡上的树林、宁静的高速公路、蜿蜒的盘山小道——车始终没有动。
在山腰上,一座被灯光打得金黄的民居出现在我们面前,门口花团锦簇,姑娘笑脸相迎。雨也停了,我们来到了一座民宿住下。
翌日清晨,雨后天晴。天空一碧如洗,世界湿漉漉的,门口的鲜花如十六岁的少女,娇嫩欲滴。满山青翠,绿得让人怜爱,大团大团神秘的轻雾快速在山间游荡。
阳光肆意洒落,荷塘非常耀眼。天高地阔,一望无边,这是一片光明的世界,被光统治的世界。
我爱这片阳光。
这片阳光就如我第一次吃到的甜甜的橘子糖。晶莹剔透,橘色诱人。那斑斓的、花花绿绿的糖纸,就如洒落在我眼前这片山岗、这片大地上的阳光,光影起伏,沙沙作响。我站在二楼的阳台,面朝东方,阳光像儿时的橘子糖般笼罩在我的身上,甜甜的,暖暖的。
可天气还是时好时坏。
阴云密布中,缆车在最高处来回摇摆,风在车厢中乱窜。山顶风很大,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俯瞰天门洞,云雾汹涌澎湃,洞内雾气环绕,团团云雾自洞中吐纳翻涌,时而袅袅生烟,时而白练似瀑,时而像一条白色巨龙盘旋翻飞、翻滚喷涌。他们说,我们真有福气,这是难得一见的“天门吐雾”。
对面的高峰是勇敢人的跳台,雾气下却显得格外神秘。时隐时现,似有似无,飘渺不定。若隐若现下,像孤独大侠的背影,头戴斗笠,虎背熊腰;又似即将拔刀征战的将军,黄沙漫天,重甲披风。
我们沿着长长的、长长的电梯,穿过山的身体,不断向下、不断向下。长长的电梯,出来后,恍如隔世。没有雾,没有风,太阳直射,天高云阔。
高高的天门洞,很宽阔。风呼呼地穿过,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水从上洒落、随风摇摆。可刚下山,乌云又起,大雨不期而至。大雨让张家界变得清爽,泥土芬芳,竹林滴翠。
十里画廊,奇峰异石、千姿百态,林木葱茏、野花飘香。但孩子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小火车。对,你说这是“孔雀开屏”,那是“采药老人”;你说这是“向王观书”,那是“三位仙女”,你们说的都对,我没有任何不同意见。
云雾又起。云雾在奇峰异石间穿梭,托起了老人、向王、孔雀和仙女。我也曾经在这些奇峰异石间穿梭、飞翔。
方圆369平方公里的武陵源,是阿凡达的故乡。在这个自然的王国,人类无法打扰,只能远远地看着,站在高山上,站在栅栏里。一座座奇峰异峦从幽深的山谷里拔地而起,刀枪剑戟、瘦骨嶙峋,巍峨挺拔、壁立千仞,危崖崩壁、遗世独立。这里本来不应该是一片绿色的世界,这里的山必须刚直、必须挺拔、必须独孤,只需保留如秦汉男人般的石壁。这里不该有绿色,不应是地球。
但一棵棵奇妙的松树,低矮瘦弱,透过石缝,抓住石壁,站在峰顶,苍郁不衰。在狂风中挺直腰杆,在风雨中仰天长啸,这些低矮的树,勇敢地闯入了他们的世界!
哪株是我?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