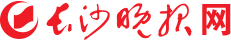散文 | 水月林畔图书香
鲁田
“读得书多胜大丘,不需耕种自然收。”这是孩提时在长沙县谷塘公社丰收大队江福田生产队双抢农忙时,从打稻机上走下来的父亲告诫我的话。正在拾稻穗的我对曾作为解放军工程兵参与建设过南京大桥的父亲是充满无比崇敬的,常常会望着霞光中父亲伟岸的身影。父亲的这句话远比“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更能引起我的共鸣。
2019年惊蛰节令前漫长的雨季里,我常常呆坐在城北高楼的落地玻璃窗前,怅望着对面学校里孩子放学穿越地下通道的身影,沉醉在课间铃声和孩子们琅琅读书声中。此时的我一如写出了《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第二部小说中刻画的那个上校,“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儿子放学归来。窗外漫天的雨幕便会凝固我漫无边际的遐想,关于读书的记忆片段开始占据我的脑海,有时我就在等待中靠在躺椅上睡着,手中的书也滑落到地毯上,我少年时负笈而行的身影慢慢溶入水月林畔的长沙图书馆中。
1980年底,母亲终于落实知青政策回城,我随母落户回到长沙。我在高考失利后进入了长沙市东区都正街街道办事处下面的一家街办福利工厂——长沙市永红童鞋厂,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五年多一直沿着幸福里、落星田、肇家坪、藩后街、水月林、平地一声雷、斗姆阁、凤凰台、县正街、都正街、火药局的线路进入天心阁西北城墙下的街办工厂;或者,从家门口省外贸局站乘坐9路车,经过老火车站、湖南旅社、浏正街、菜根香、浏城桥、定王台市长途汽车站一直到工农桥下车,步行下古稻田的陡岭进入工厂。
不足百人的街办福利工厂很小,是一家是以残疾人为主体的手工作坊企业。一二楼都是车间,设计室和仓库在三楼。那时资料很少,位于小巷深处的长沙图书馆因为在我上下班的必经路上,我便常常去图书馆,查阅制鞋设计及皮革保养的专业书籍。不久,领取了第一次月薪的我欣然用近四分之一的工资、一张工农兵大团结的10元钱作为押金办了一张蓝色封面的《长沙市图书馆借书证》,一人一证,一次一本,最长借阅期15天。
不久,我中学邻座陈玲同学被招录进市图书馆工作,恰好分配在二楼外借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过如此,我从此如同其他资深人士享有一次同时借阅两本或三本的便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等辞书,售价是九块八一本,新华书店一册难求,常常排起长队购书。限于财力,当时找邻居借了20元去新华书店排队也没买到,只有走图书馆预约外借新版图书的路子。有了同学介绍,馆领导给我开了绿灯,我便如饥似渴摘抄了大量自己喜爱的诗词,文学素养也就自然渐长。接下来,图书馆中借来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再加上享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完全改变了我的理解层次,思想与境界从小吴门深处那条青石板老巷,飞越到迫切想见识的外部世界。
清晰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聂卫平九段在连续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以11连胜,连续为中国取得了三次擂台赛的胜利,全国形成了一股围棋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下围棋。然而,当时围棋书籍却少得可怜,书店里根本买不到,图书馆的藏书自然成了棋友争阅的香馍馍。因为同学的情谊,她会常常为我保留一些还回的围棋书籍,并通过168台给我的汉字BB机留言,我出差归来马上会去借阅。就这样,《围棋战理》《中国流布局》《围棋攻防技巧》《弃子的魔术》等中日高手专著让我棋力突飞猛进。
1992年,我成为长沙市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1995年散文《木屐》在《美文》杂志刊发,不久选入中学语文读本。我也从工厂招入当年路过时仅梦想能上文章的湖南日报社工作,成为记者,后招考调入人民日报社教科文部。
2016年,我和棋友在常德澧县城头山主办了中国首个业余围棋杀猪大会,我写赋:“云梦泽畔聚八方仙友手谈贺新年,金猴助尔猎神猪。千古无同局,彭山钦山俱通幽。壶瓶山里藏万缸好酒一醉辞旧岁,锦鸡迎君执牛耳。落花人独立,沅水澧水皆属我。”
围棋与读书,相得宜彰。琴棋书画,俱在细微。当年摘抄的锦句名言常可脱口而出,在微信盛行的今天,读书的妙处需要慢慢去品味。
一路走来,腹有诗书气自华,最忆水月林畔图书香!
>>我要举报